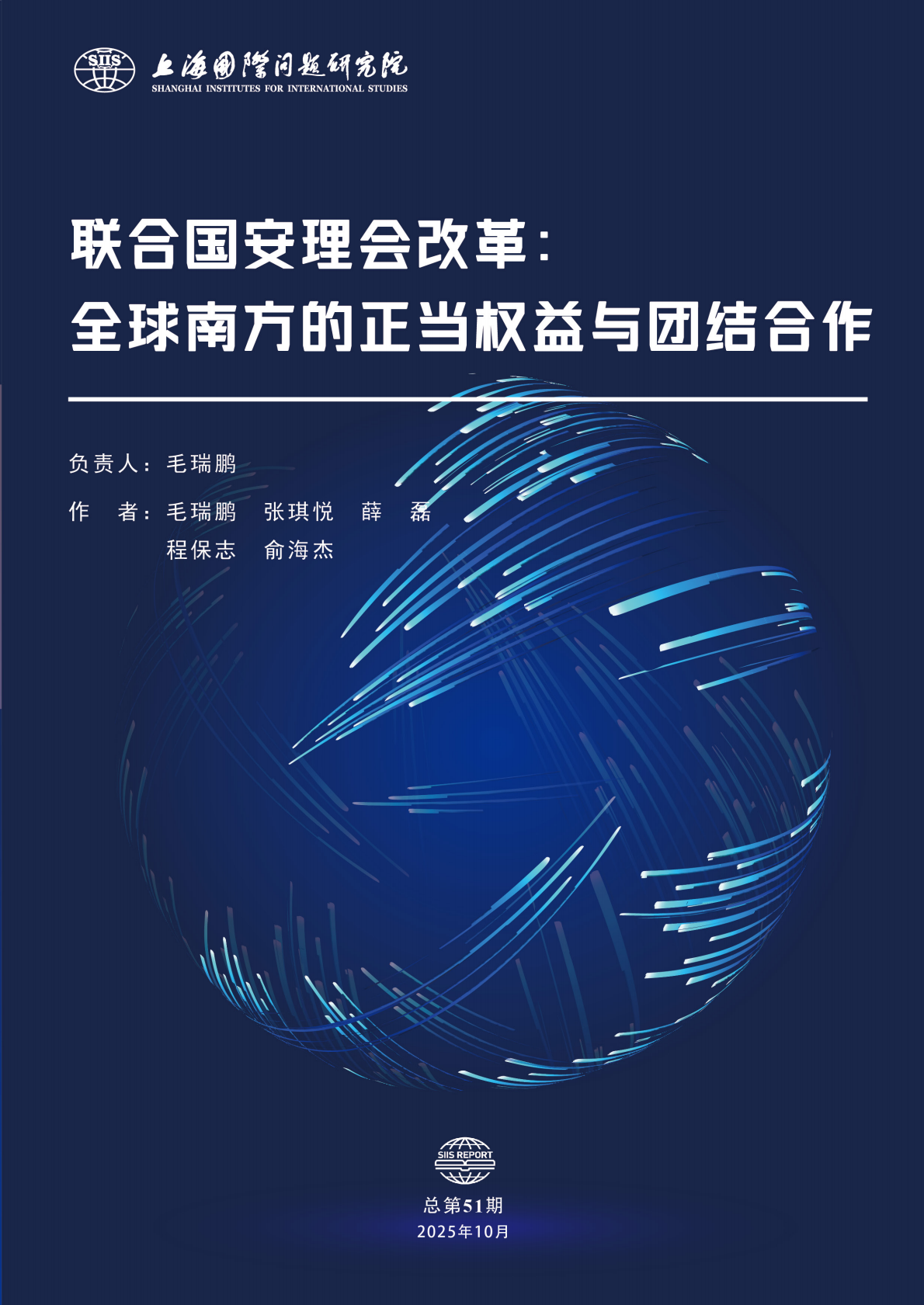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全球南方的正当权益与团结合作
薛 磊 张琪悦 程保志 俞海杰 毛瑞鹏
在二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承载着世界人民“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期望,是人类追求世界和平与公平正义的思想结晶和实践成果,其诞生为全球治理“掀开新的一页”。安理会是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安理会的工作成效及改革走向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安理会由于成员构成不公、代表性不足,其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亟需通过改革反映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客观现实和历史潮流,以增强其机构合法性和提振国际社会团结协作的信心。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球南方主要指代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集合体,涵盖亚洲、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全球南方国家在历史遭遇和发展阶段上面临相似的处境,在国际制度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全球南方国家在数量上占联合国会员国的大多数,不仅是安理会议题的主要聚焦的对象,而且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有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决策层面长期处于相对边缘地位,在议程设置、投票权重等方面的话语权明显不足。
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使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利益与核心关切难以在安理会机制中得到有效反映,制约了其在国际安全议程中的参与深度与决策能力。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代表性缺失正在削弱安理会的治理效能,并对其合法性构成实质性挑战。一方面,由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意见未能在安理会的决策过程中得到充分表达与重视,使得安理会在应对涉及全球南方的安全事务时,常常忽视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背景、发展诉求与安全观念,可能忽略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利益,难以实现普遍包容与文化多样性的治理目标,从而制约其治理绩效与政策回应能力。另一方面,决策机制中代表性的缺失,持续削弱全球南方国家对安理会的制度信任,其对联合国整体合法性的认同也趋于弱化。在缺乏平等参与和有效表达的情况下,南方国家越来越难以将自身利益诉求纳入安理会议程,产生制度疏离感和参与挫败感。在制度运行层面,这种结构性失衡不仅影响联合国各项安全决策被接受的广泛度,也削弱了其凝聚多方共识、统筹全球响应的能力,进一步动摇其作为全球治理核心机制的有效性与权威性。
全面审视全球南方在安理会中的制度地位、结构性障碍、改革诉求与合作实践,既是对历史制度不平等的必要回应,也是推动构建更具代表性与治理效能的全球安全架构的现实要求。基于此,本报告立足全球南方在安理会中的实际角色与制度参与现状,系统梳理其话语地位的历史变迁与现实约束,分析其核心主张与集团诉求,评估现有合作机制的作用与局限。为推动实现更加平衡、包容和民主的国际安全治理秩序,报告进一步提出政策性建议,为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推动安理会改革朝着更加平衡、包容与高效的方向发展,使其结构与功能更符合当代国际格局,有效提升联合国的权威性与行动能力,为全球和平与安全提供更有力的制度支撑。
报告认为,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与发言权,需从四方面集体发力:
一是维护《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宗旨和原则,强化改革合法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安理会改革的“根本遵循”。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尊重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改革诉求高度契合。南方国家应将安理会改革诉求与《宪章》紧密结合,巩固道义与法律支撑,应对美国单边主义冲击。
二是聚焦可行路径,寻求最大公约数。在世界动荡变革和多极化加速演进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应坚持行动导向,平衡理想与现实,优先推动扩大非常任席位、优化区域轮换等共识度较高的议题,同时以“增强联合国效能”为诉求基调,争取广泛国际支持。
三是加强团结协作,提升集体行动能力。全球南方的国际影响力来源于团结合作。为此,应加强全球南方制度化协调机制,完善常驻联合国代表会晤机制、“77国集团和中国”磋商等平台,形成联合提案;构建议题导向型联合阵线,围绕气候安全、人道危机等组建“议题联盟”,提升议程引领力;加强能力建设,由中、印、南非等牵头开展外交培训,建立专家库与智库联盟,缩小知识与能力差距。
四是引领安全议程,拓展制度性话语空间。主动创设“全球南方和平倡议”等平台,借鉴“和平之友”小组等经验,形成南方治理范式;利用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制定议题清单,轮值主席国期间主动设置议程,同时加强与前后任成员衔接,确保政策延续性,逐步实现从“治理对象”到“议程引领者”的转变。